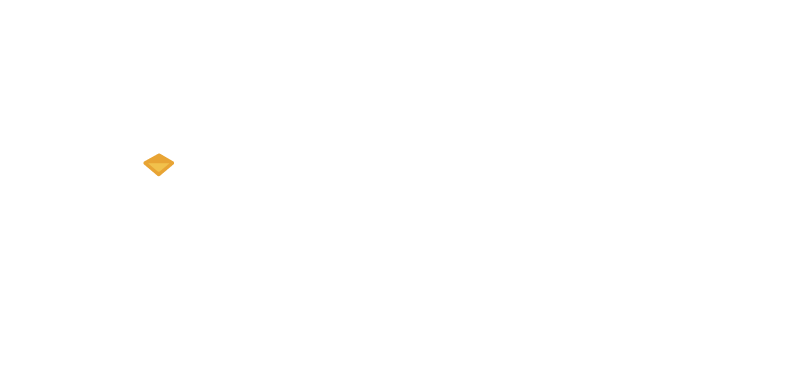粉丝社群
有人的地方就有崇拜和追逐,随之也就产生了“粉丝”。“粉丝”,指某人、某事物的喜爱者、崇拜者,自古有之。
如戏迷、票友就是“粉丝”的别称,而张籍“焚杜甫诗饮以膏蜜”,“看杀”卫玠,郑板桥自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等过往轶闻也成为了古代崇拜者们“追星”的实证。

“粉丝”一词正式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 2005 年湖南卫视歌唱类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播出之后,由英文单词“fans”音译而来。直到今天,体育竞技、企业品牌、金融教育等各领域名人名物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都可以被称为“粉丝”。
共同目标、高效协作、一致行动是社群构建的基本要素,学者蔡骐提出,在社群中粉丝通过风格的实践,彰显个性并且构建文化资本。粉丝社群以粉丝们围绕特定对象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其中包括网络粉丝社群。

网络粉丝社群是以站子为基础,以贴吧为中心,对内向成员提供意义生产和认同建构,对外代表粉丝群体与其他对象互动的组织。但随着微博等多类社交平台对市场的争夺,贴吧的社群运作优势被其他平台复制甚至超越。
如微博不仅可以为粉丝成员提供私密讨论的空间,粉丝还可以在微博中进行宣传;而在微博超级话题功能开发之前,一些明星 QQ 部落就成为了粉丝们较为隐秘的活动空间。

因此,本文认为,粉丝社群是:由有共同偶像的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组成,具有高度的群体认同及一致的群体目标,并且能够开展秩序化、规范化行动的粉丝集合体。
娱乐明星粉丝社群
娱乐明星粉丝社群作为粉丝社群的分支,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娱乐明星粉丝社群成员,指的是那些喜爱崇拜某娱乐明星并自愿予以资金、劳动支持的人,因此娱乐明星粉丝社群即由娱乐明星追随者们共同组成并在其中展开社会交往的粉丝集合体。

与一般的粉丝社群一样,娱乐明星粉丝社群也是以社交平台为主要活动场所;但不同于一般粉丝社群的是,娱乐明星粉丝社群的传播力与组织性更强,资本的倾斜也为粉丝社群的成熟注入动力。
不过资本介入社群运作,在另一方面则为社群发展注入了极端、功利的商业逻辑。除了外部资本,社交平台也在娱乐明星粉丝社群的塑造中起到重要作用。

进入互联网社交时代,社交平台为娱乐明星的粉丝们交际提供空间,粉丝之间的交流愈发频繁和即时,凝聚一个社群变得更加简单,关系也进一步走向亲密。
基于此形成的社交平台粉丝社群具有很牢固的交流“壁垒”和圈层属性,通过设置语言符号、知识资产等门槛打造了严防“外来入侵者”的“社群桃花源”。
壁垒的设置一方面保护了社群内部的纯洁性及社群传播活动的安全性,但另一方面也构造了一个巨型的“回音壁”与厚重的“信息茧房”,给内部激进的情绪和极端的观点提供了生长的温床。

娱乐明星粉丝社群传播的产生条件
娱乐明星粉丝社群在社交平台的传播活动以共同偶像为中心展开,既能在交往中保持粉丝社群内生态活性,又能不断激励粉丝热情与责任感为偶像不断生产“数据”。
技术进步支撑社群构建
媒介技术的优化升级为粉丝社群的发展提供机遇。首先,媒介技术进步为明星们带来了更多“前台”展示的机会,他们的个性、才能、故事及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在文字媒介时期,人们只能通过现场的狂欢感受明星直观的魅力,或者通过口口相传与文字作品了解明星;进入读图时代,明星们的音容笑貌被定格在闪光灯下,镌刻在胶卷中;
音视频时代的到来,则让粉丝们能够更加直接地感受偶像的魅力,再华丽的语言也没有生动的画面让人记忆深刻,试想如果没有《胭脂扣》这部电影对“十二少”的风华记录与传播,演员张国荣的神态性格再天真无暇,也难以让粉丝们至今还难以忘怀。

其次,粉丝们也能够通过更多渠道加深对明星的了解,并凝聚成具有合意的社群。人们很难仅仅根据单一渠道或短暂接触就从路人变为某明星忠诚的粉丝,大部分只停留在“三月剧粉”的阶段,但媒介技术能够通过促进各类平台发展,为粉丝提供了解明星的渠道。
如粉丝可以通过微博热搜榜单等了解一个明星,也可以在腾讯优酷等传统视频平台自主观看明星的作品,还可以从 B 站等平台搜索更能引发共鸣的饭制视频。

娱乐工业激活粉丝力量
在娱乐工业中,粉丝是文化消费群体中最富活力的一部分,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西方国家娱乐产业体制改头换面,粉丝群体的地位逐渐得到商业机构的肯定,其话语权与影响力蒸蒸日上。
在我国,上世纪末香港娱乐圈的“四大天王”就是由资本主导产生,粉丝只是居于末端的消费者。

粉丝对明星的消费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性较弱的消费,明星类型由投资方选择,明星的事业方向也掌控在唱片公司、电影公司等投资方手中,粉丝的选择权实际上是有限的,如张国荣拍摄《胭脂扣》这一作品,是香港嘉禾公司与新艺城公司的利益互换。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粉丝文化的起源盘根错节,香港的资本造星路径也一起迁移到了内陆,因此我国在 21世纪初期存在着很长一段的资本造星期。

以 2004 年《超级女声》为例,即使粉丝可以通过发短信投票的方式支持选手,但粉丝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造星”流程的透明度也值得怀疑,最终掌控着整个局势的还是节目制作方“天娱传媒”。
新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激活了粉丝在追星活动中的能动性,粉丝的力量得以凝聚和凸显,娱乐工业也尝试着将更大的控制权交到粉丝手中。在新媒体时代,粉丝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明星信息的方式反馈自己的情感及意见,明星的影响力及价值量逐渐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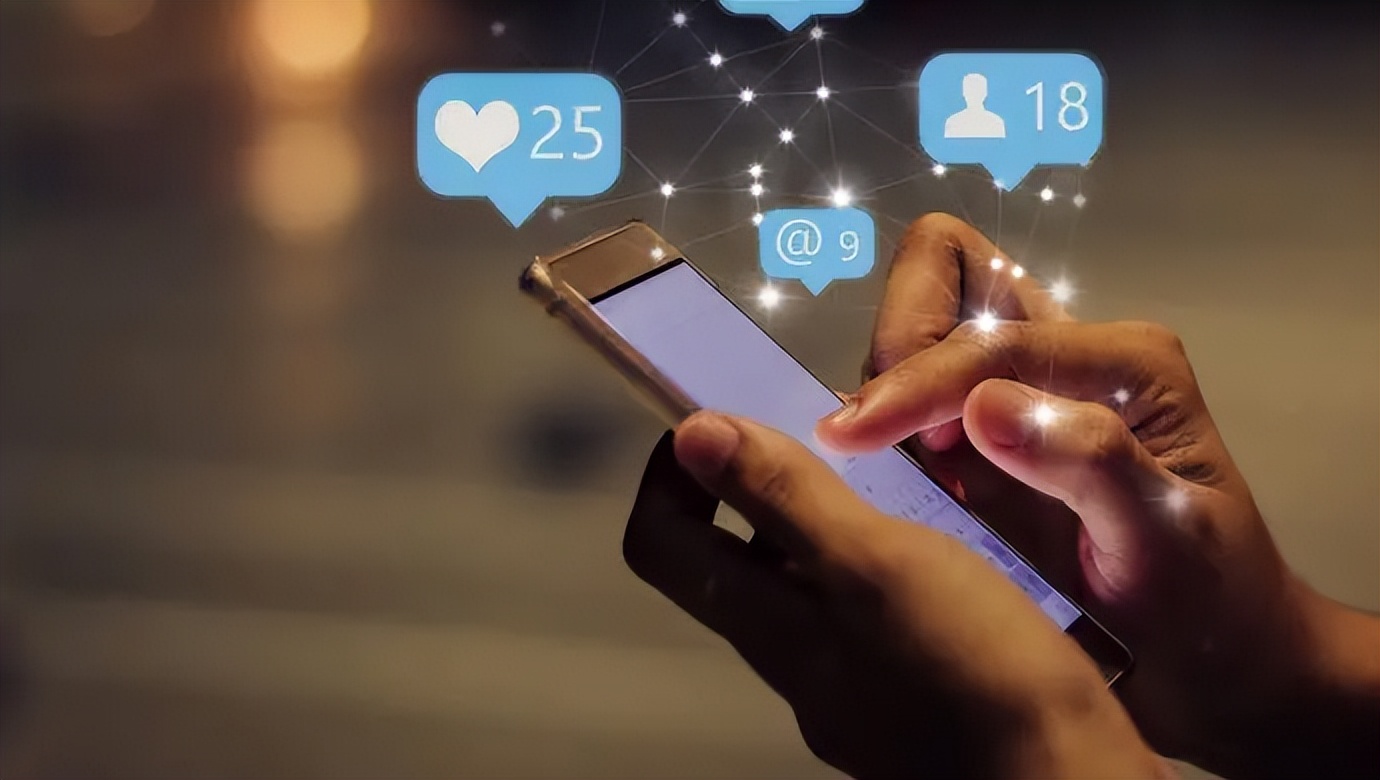
到现在,除了可以通过购买明星代言及杂志周边等方式表达支持,粉丝甚至还能成为造星者。如 2018 年视频平台爱奇艺播出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就赋予了观众“全民制作人”的身份,全民制作人们可以通过投票“制作”符合他们期待的偶像。
经纪公司会不断组织比拼来把握准明星的被喜爱度,只有能让粉丝无私付出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出道机会。社交平台使得粉丝们能统一行动,让粉丝能量完全得以释放,而不至空有“一腔热血”但却无处施展。

媒介化社会孵化趣缘群体
媒介化社会描述的是社会与媒介进一步深度融合,表现为社会化的媒介与媒介化的社会两种。
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对媒介的依赖逐渐加深,最终演化为以媒介为中心的生存形态,媒介作为一种工具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中介物,媒介也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娱乐明星粉丝社群系统与媒介系统便在互动中构建出新的系统关系。

在媒介化社会中,社会互动的公共领域由传统线下场所转为虚拟网络场所,媒介拟态环境的设置权也从专业媒体泛化至普通大众,人们认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空间渐渐趋向部落化和标签式的人群划分。
也就是说,媒介发展并未在真正意义上为我们带来全社会的互融共通,反而是将人们进行了一次“再部落化”。

分散性的粉丝也在媒介的不断发展中以共同兴趣为依据相互吸引并聚拢为趣缘集合体,逐渐进化出社群规范及身份认定机制,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围绕共同的议题展开互动使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和广泛分散性的粉丝社群。
但也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圈层性特征,使得粉丝社群对意义的编码解码容易与主流解读或其他圈层解读发生冲突,造成价值冲突和伦理失衡。

随着媒介影响力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进一步加深,人们从主动追求媒介消费向依赖媒介与被迫接受转变,媒介消费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和空闲时间,也成为人们物质需要及精神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的必需品。
在媒介的影响下,个人自我式的媒介消费被群体分享式的媒介消费所覆盖,媒介消费的过程成为互动交流的过程。

当下受控的偶像也可以看作是被消费的媒介,粉丝在进行偶像消费的过程中不止满足于实现自身需求,还渴望通过粉丝间的共鸣得到认同,娱乐明星粉丝社群就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了。
社交平台娱乐明星粉丝社群传播的产生条件
社交平台是娱乐明星粉丝社群传播的基本场所,社交平台的发展让各地粉丝的凝聚成为可能,同时也能满足粉丝的各类需求。娱乐明星的粉丝社群并非原子式的集合体,而是具有一定理性色彩的组织,享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也就是说,娱乐明星粉丝社群还是相对成熟的社会组织,既有对行业规则和平台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有立足于偶像未来发展的长远眼光,能有效提升粉丝社群的传播效率。
在社交平台产生之前,粉丝基本只能在官方公开消息中了解偶像的行踪,但社交平台网状的传播链条为粉丝追星摆脱了滞后性,带来了更为即时的小道消息,粉丝阿木称“加入粉丝社群后,信息来源变得更多元更及时”。

这一社交平台与生俱来的特性使其成为娱乐明星粉丝社群传播的最佳场所。社交平台之所以能成为娱乐明星粉丝社群的发源地,与其管理和规范也分不开,正是这一些规范让社交平台与娱乐明星粉丝社群实现共生。
如微博设置的“删除评论并拉黑”功能,能够让用户能够自行维护自己的评论区,部分用户还享有这一功能之外的附加功能——被删除评论的用户将失去近三天在微博社区的发言权。

出于维护偶像及所在粉丝社群利益的目的,娱乐明星粉丝社群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且量化的数据也加剧了粉丝在传播中的紧迫感,主动的媒介消费变为被动的生产。
无论是通过不断进行数据劳动凸显偶像的影响力,还是通过提高社群互动频率凝聚粉丝力量,都是围绕偶像利益进行的“赶工”式传播。

对于由无数松散个人组成的粉丝社群而言,只有树立共同的目的并实施不断的奖赏才能在社群内形成合意,将粉丝社群的力量释放到最大,外界的正面评价对粉丝而言就是一种重要的奖赏。
如为提升偶像的社会形象,粉丝们组织以偶像的名义做爱心公益,如王源粉丝在山区建立“王源信号站”,王一博粉丝打造“王一博公益小屋”为青少年提供物质帮助及精神食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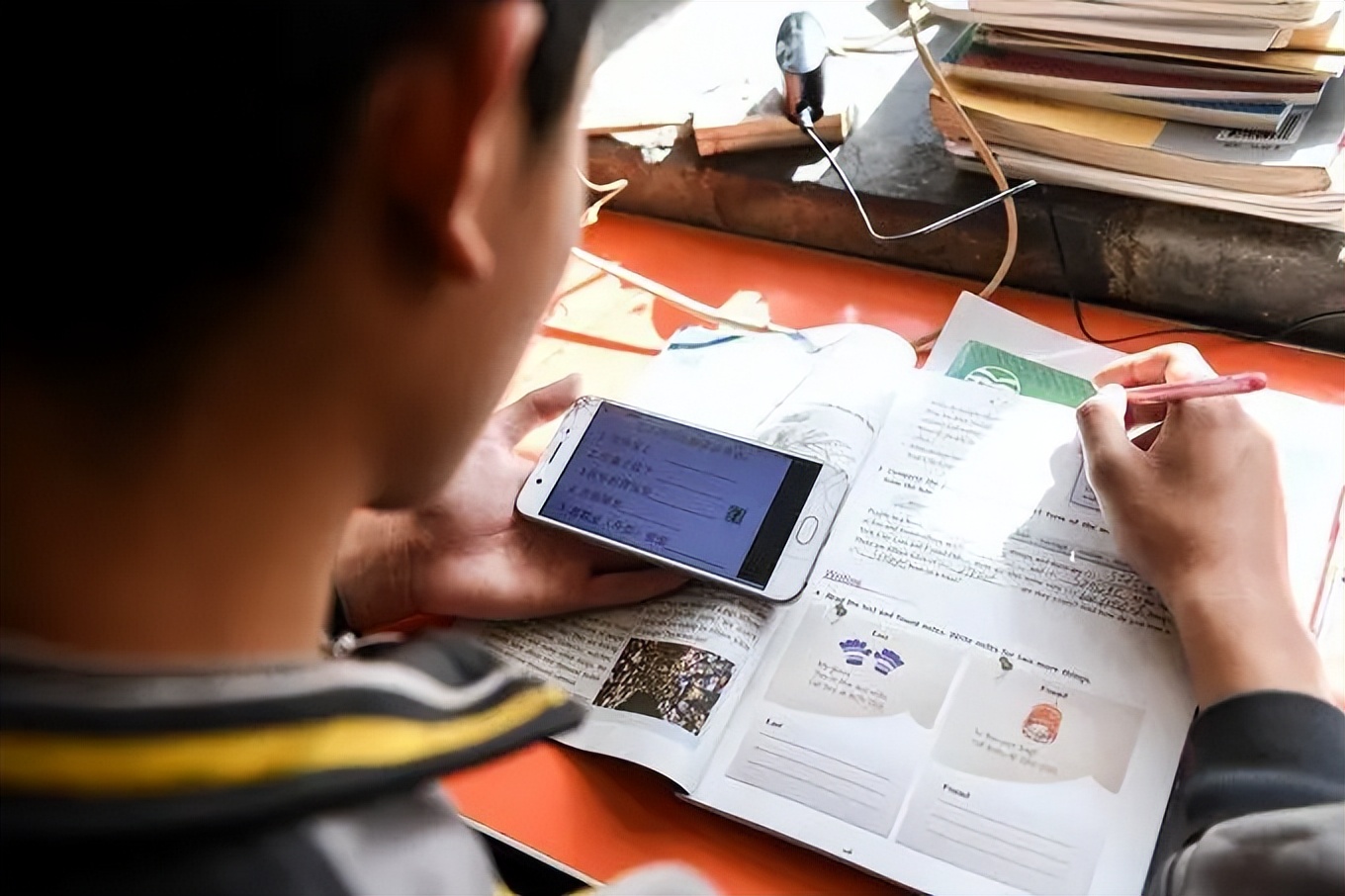
粉丝的公益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隐匿的传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削弱了部分社会公众对娱乐明星相关信息的抵触心理,进而改善脑海中关于该明星的印象。
需要注意的是,粉丝们虽然可以通过维护偶像声誉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但也让自身困于他者的审视和数据囚牢当中。